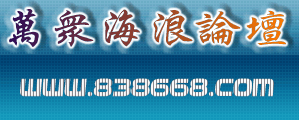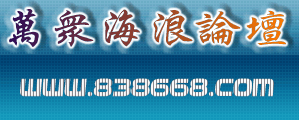【导读】栓子此时忽然想起村人讲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曾经有个妇人在河边洗衣,水中便旋起了漩涡,就把女人卷走了是王八精干的!一想到这,吓坏了!不能让她下水啊.....
一
李翠花大肚子已经被人看出来了。 因为这事公社计划生育办的找她两趟。 在公社碎石厂拉碎石的车老板栓子对翠花说:你就去医院弄掉吧,要罚,咱家可没钱。 李翠花天天为这事忧心忡忡。眼看着放了暑假在家玩的两个孩子,还是觉得一个男孩孤单。之后的日子,她天天想办法。她突然想起了多年不见的表姐来,我就是藏到那里安全,连栓子都找不到。 栓子赶车回来,累得臭死,夜里翻来覆去的,一点没心思摸翠花的奶子。他忽然想起今天见到城里的同学了,搡着睡不着觉的翠花说:再等三天,八月节了,咱不用买肉了,同学说给我一张肉票。你听到了吗?翠花哼哼着,心不在焉。 八月节头一天,翠花没去生产队干活,去赶穷汉子(土语)集。 卖肉的老张看到翠花身怀有孕,就撺掇着:来,翠花,买几斤猪肉吧,孩子出生有奶水。 啊,还买肉呢,等着挨罚吧。 挨罚,也得吃肉啊?来,割点。 翠花真想买肉,咽着口水说:就割五斤,肥的。 肥的贵,连肥带瘦都来点。结果,老张给割了六斤。弄得翠花多掏了八毛钱。 八月节栓子上了半天的工。车一停在生产队,就高高兴兴地拎着五斤猪肉回来了。一边进屋一边喊:翠花,翠花,快看,这猪肉好啊,肥的多。翠花正在炒猪肉芹菜,小碟里已经弄完了拌的凉粉条。哎呦,你高兴啥呀?我昨天都买肉了! 啥?你买肉了?谁让你买的?你没听说我要肉票了吗?你这个败家的老娘们! 翠花一脸委屈,我败家了吗?你有肉票也没跟我说呀?我败家是给你泼米了?是撒面了啊?啊? 栓子很生气,肉票的肉和买的肉差一半钱呢。就抡起大巴掌,臭娘们,我让你犟嘴,啪就是一耳光。 翠花哭了,拾掇包裹。你打我,打吧,我不愿意天天受你气,不过了。栓子像是不解气,还用拳头擂她。孩子哭着喊着拽着,怎么也拽不住。 翠花拎着包裹跑过老哈河,上了岸,等上了去宁城的班车。从我们建平到宁城一百多里,栓子怎么能找到?再说,他也不知道有这个亲戚啊?
二
翠花是一去不复返。她一直都在表姐家。孩子四岁那年,她想领孩子回家,表姐就是不给她。表姐是国营工,只有一个女儿。把翠花气得跑到那片废墟上。她突然好奇地重温一下旧梦,就迈着闲散幽怨的步子来到那片破瓦房处。那里不知是倒闭的厂房还是学校,现在被铲车铲得乱七八糟,多数是房产开发。春风中,鲜嫩的蒿草冒出幼芽,在那里招手,像是欢迎多年的老朋友。翠花想着那片破屋檐,就慢步来到那里。扑腾腾惊飞一帮麻雀,打那边也走来一个人,让翠花惊呆了。 这个男人不是栓子,叫李哲。 这些年,栓子一直在碎石厂往站台拉碎石。一天,一帮社员往火车箱里装碎石,打开车箱,发现里面蜷曲着一个讨饭的,满脸的煤黑。人们把她拖出来,发现是个女的。当时社员好闹,就喊大栓:栓子,快,把她领家去吧,你正好没媳妇。栓子憨憨地笑着,看一眼脏兮兮的女人,呵!真脏。我可不要。 社员们都奚落这个脏女人。栓子说:干啥呀,你们这是人家本来就是要饭的,不给口吃就算了,干嘛欺负人家啊? 哈哈,大闺女要饭死心眼子。有的人竟出言不逊。 其实这个女人叫吴丽丽,因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受了连累,从南方跑出来,踏上了列车,就晃荡到这里。 社员们闹着,对栓子说:你看不惯,就带她回家呀? 栓子挠挠头皮,她要跟我回去,我就带她。吴丽丽像遇到了救星,跟着他就走。栓子就把吴丽丽拉回了家。栓子让孩子管吴丽丽叫姨。栓子找出了自己女人穿的衣服给她换上。她把脸洗干净了,却是个活脱脱水灵灵的大姑娘。闲谈时,栓子了解了吴丽丽的遭遇,问过她婚姻情况,吴丽丽说尚未成婚。她态度明朗,只是下乡时谈过恋爱,现在不知那人哪去了。栓子说:你原来是知青啊?孩子不在时,吴丽丽冲着栓子笑着说:我这样的走资派的女儿,嫁不出去啊。栓子安慰道:你别胡说了。那嫁给你,你敢要吗?把个栓子说得脸红红的。栓子解劝着说:我是有媳妇的人啊?我已经对不起媳妇了,不能再对不起她。她虽然跑了,但我们还没有离婚,她早晚能回来。 这样,一住就是四年。吴丽丽怨恨地对栓子说:你是死人啊,不懂人家的心?四年了,我都没走,你不愿意娶我?栓子和孩子们对吴丽丽都有了感情。一次,下起大雪,吴丽丽跑到中学去给大女儿送厚棉衣,送咸菜,把自己弄得浑身湿透。孩子的心里能不装着爸爸捡来的妈妈吗? 吴丽丽有时撒娇地往栓子身上靠,想要点温存,栓子就是坐怀不乱。孩子们大了,劝爸爸娶了姨,撵姨去爸爸屋里住,都被栓子阻止了。 栓子说:等等吧,翠花一定会回来。 有时栓子就想,我是不是让吴丽丽给改变了?我当年对翠花这样,翠花不至于跑吧。也不是,我就是这个脾气。不过,打吴丽丽来,我还没有打人。还是她给改的。翠花跑,不能是一个原因,她一定是出去生孩子去了。 吴丽丽在栓子家呆了四年,不论外面怎么流言蜚语,栓子自觉问心无愧。吴丽丽是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走的。 栓子站在村头,挥着手:走吧,走吧,有啥难事再回来找大哥。 林带里静悄悄的,偶尔一阵风吹过,捎来成熟的庄稼的气息。吴丽丽猛地转过身,跑到栓子跟前,一下子就搂住栓子大哭:哥哥,我不想走 栓子推开她,擦着她脸上的泪,走吧,丽丽,你要想着大哥,就回来看看。
三
那年中秋节,没下车时,天空就乌云密布。后来雷电交加,大雨夹杂着冰雹。 车在客运站外抛锚了。翠花下了大客,用衣服遮着风雨没跑出多远,躲到一个人家的大门洞子底下。天,好黑好黑,一个接一个的雷闪,雨夹杂着小粒的冰雹,一阵紧似一阵地下。雨水中,踉踉跄跄地过来一个黑影,翠花借着闪电一看,是个男的,浑身湿透!没等多想,这人就像醉汉一样,摔倒在翠花的身旁,翠花知道,他肯定是跑到这避雨的。出于仁爱,翠花不得不上前拽他,可能是冻的,他就像是一尊僵尸,一动不动。任凭翠花怎么喊,怎么搡搭,还是不动。翠花四下瞅瞅,五米之外,看不到人影,被雨水淹没了。翠花想离开这里,外面的雨一刻都不停,老天像是和她作对。翠花挓挲着手丫一时没了主意。这里就一两平米那大的地方,她想拖他往里点,自己靠外,抵挡着斜射进来的风雨。当她拖他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他的衣服太湿了,都能拧出水来。他真的冻僵了?会不会冻死?翠花虽然有些害怕,可她不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啊? 这是一个四十左右的男人,个子也不算高,穿翠花带的衣服,也能穿,翠花就翻他的身,把他的衣服往下脱,上衣、裤子全脱了,把翠花累了一身汗,为了救他,也不顾什么男女了。翠花的脸也没觉得红。 衣服换好了,那人依然没醒。这可咋办?翠花更加为难了? 雨,一直下个不停,凡是低处和水沟,都淌满了水。翠花开始敞开怀,为了救人,把他抱得紧紧的。那人刚刚发出一点微响,翠花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她的乳峰像两座高山,不由自主的抵压着男人宽大的胸怀,翠花的心剧烈的跳着,等待着他复苏的一刻。 不知这里是一个破厂子或学校,空空荡荡的。破檐顶上滴滴答答地漏了雨。天快黑的时
北京中科医院电话候,那人觉得胸前一股暖流,挣脱了翠花的怀抱,如梦方醒。 我是被雨浇的,你是?哦,是你是你救了我?他半靠着墙,扶着墙站起来。 翠花忙起身,系衣服扣子。脸上火烧火燎的,浑身在颤栗,连胸前那鼓鼓的双峰都一跳一跳的。她着实是冻坏了,为了抱住他,用尽了全身的热能。何况,后背还得接受顶部的雨淋,下方还伸着两条腿,屁股坐在冰凉带着微湿的地上。 他打了一个寒颤。哆嗦地看着翠花: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为啥救我呀,我是早晚要死的人啊? 翠花不明白咋回事,忙在包裹里找衣服,我还有一身衣服,你快披上! 你不冷吗?你穿。当他低头的空,瞅见自己,哎呀,你啥时给我换的衣服呀? 你一跑到这,就浑身湿透了,我就给你换了。 哦!他想了想,半天没有言语。 你咋不说话了? 嗯。我是想,我要死的人了,留着钱也没有用。 你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啊? 他忙着去找自己的衣服,小春拎过湿得能拧出水的衣服说:在这呢! 我是杀人犯,从家逃出来的! 啊?翠花大惊失色,拎起包裹,要跑到风雨中。 你别怕!他一把把她拽到身边,你救了我,我还得报答你呢 翠花无法挣脱,被他使劲这么一拉,又一次拥到他的怀里! 夜,飕飕的狂风,夹杂着雨,一个劲地下,真是和翠花作对啊!吧嗒,吧嗒,上面开始掉泥。翠花吓得张大嘴巴:你想把我怎样? 那人急忙放手,我我,脸颊绯红。忙去衣兜里,翻东西。翠花趁他翻东西的空,又要跑。第二次被他拽回!妹子呀,你咋这样?我还没问你是哪的人?跑出去,不得让雨淋死?翠花还是想逃脱,淋死?也比救个杀人犯强!翠花的牙关偷偷地咬得嘎吱吱响,他要对我不利,我就和他拼了!
四
他战栗的手从衣兜里掏出厚厚的一打洇湿的大团结来。 翠花紧张的喘着粗气,不敢正视他。他拿着这些钱,数着,有一千块了,停了下来说:大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没什么报答你,这一千块钱,你收下! 翠花回头看着他递过来的钱,摇摇头说:我不要,救你,钱我也不要。 他硬是往翠花的手里塞,大姐你别嫌少,这辈子无法报答你了,我是个要死的人,要钱还有啥用?说着说着,一个大老爷们,啼啼哭哭的哽咽起来。 我忘了问你了,你是哪的人?为啥杀人啊?翠花突然发问。 咳!父母头些年被下放到农村,处个对象是个走资派的女儿,被那个耀武扬威的人打了。我便怀恨在心。后来,终于熬到云开雾散,我回城了,在凌钢当了一名职工。那天夜里,我稀里糊涂地看他向我扑来。我猛然惊醒,这不是我多年的仇人吗?正好,身边有把剪刀,我拿过来,朝他的喉管猛刺过去。他哼了一声,躺在地上,翻来覆去地打滚,我看他没死利索,上去拔出剪刀,又补了十几刀,直到他停止了呼吸我穿好了衣服,摸摸口袋里的钱鼓鼓的都在,就仓皇而逃。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他支吾着,我?既然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也不瞒你了,我叫李哲。 我是拉碾子沟的,我叫李翠花。 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你是拉碾子沟的?我妹妹就在那里下乡来,她叫李英,后来返城了。 他又俯身拿起衣服,掏那打钱,好像不给翠花这辈子也不心安。他举到翠花的怀边,非常诚恳地用温和的带有一点哀求的语气:大姐,你就收下吧。 过半夜,雨才停。两个人一直等到亮天,才互相告别。他说:我也只能穿着你的衣服走了,我的衣服我拎着,将来我要到拉碾子沟看看,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有缘的话,一定去见你!并嘱咐翠花:一个女人,要处处留神! 翠花想,我和你要是有缘,将来有了钱,你要被判刑不死,我一定还你!一千块钱啊! 他啪嗒啪嗒地跳进了泥泞里,翠花和他分道扬镳。
五
翠花想去那个地方走走,突然遇上了李哲。 这种久别重逢的惊喜,像一杯杯很浓很浓的烈酒,把两个人灌得酩酊大醉。这里比较隐秘,有破门楼挡着,他们跑到一起抱了一下,马上就放手了!两个人,只抱那么一瞬间,就已经感到窒息。她突然伸出手,拽着李哲破夹袄的袖子,来回地抡,又双手对着李哲的胸口咚咚地擂,杏眼睁成大大的问号,大声嚷着:你坏!你真坏!你不是杀人犯吗?翠花觉得自己略显轻浮,退后一步,细细地打量他,滚烫滚烫的脸融化了西天的霞彩,眼里放射出火苗,要把李哲烧焦:你真是个骗子! 翠花故意转过身,装做不理他欲走的样子,李哲也觉得刚来时的冲动,不好意思地拉了一下她的手,你真走啊?我不能骗你,我真是杀人犯! 翠花转过头,甩了他一下手,发出疑问,一个杀人犯,逃跑了三四年,就没人抓? 李哲装作很镇定,严肃得一本正经:你难道盼着我被抓起来吗?翠花忙解释:你看看你,我哪有那个意思呀?我是说,一个杀人犯这多年会逍遥法外? 闹了半天,还是那个意思。 翠花急了,紧地摇头,不是,不是,你别强词夺理! 李哲又抡她一下手,好了,别嚷了,这地方多亏安静,要不然,非让人把我抓去不可。先说说你吧,咋跑这来了? 翠花说,我来这里看看,你呢? 我?我也来这里看看。真是奇怪了,我们真是有缘分。 你打算去哪? 咳,天天躲着呗。 你不嫌弃,随我去表姐家吧。在那里躲一段时间。
六
翠花拉一下李哲,他尾随着她,低着头走。他故意让翠花离他远点,畏缩着,怕路人投来那种莫名的火辣辣的目光。翠花特意放慢了脚步,等他一下,回过头,继续拉他,他不自然地一躲,说:我跟你走就行了。 你怕啥呀?我都不怕!亏你还是个大老爷们? 我李哲只是低着头。跟着她默默地朝前走。 正思忖间,来到城郊外的一片宅区。透过杨树的枯枝,看见掩映在那里的矮趴趴的瓦房,又绕过一条污水沟,直往前行。呼平地刮起了一股大风,席卷着黄沙,打在两个人薄薄的棉衣上,两人都打个寒颤。李哲缩着身,一只手轻揉迷进眼里的沙尘,掉下两滴浊泪。呵!这股旋风,真大!翠花说,这春天,风沙就是大,谁也没办法,看来,天又要起风。她指指天空一丝丝绒带般的云絮说:你瞅瞅,风,一刮起来就三四天,把人烦死,看云彩,就是刮风的征兆,和拉碾子沟没什么两样。 李哲说,刮了风,天就冷了。 也不是,你看那水都流得急,现在是冻人不冻水了!人的汗毛眼儿开了,春天一有点冷,人就不经冻。 过了林边的一个厕所的小独房,在头一溜街上第二家,就是翠花的表姐家。虽是一片破瓦房,却很安宁和谐。两个人风尘仆仆的钻进了屋,翠花喊:姐 翠花的表姐五十多了,两人长的有点相像,忙迎过来,姐夫和孩子也往这边瞅。 翠花,早就等你吃饭了,急死人了! 表姐问翠花,这是哪的客人?翠花敷衍说,我同学。好,我去拿双筷子,拿碗,一齐吃饭。正说着,窗户被风吹的咣当一下开了,冷风夹着烟尘嗖嗖地刮进来,都刮得桌子上的筷子在滚动,表姐赶忙摁住盖饭的盖帘。姐夫跑过去关窗,嘴里在嘀咕:这破房,窗户都关不住,天天说分房,也分不下来。翠花插嘴道,我看街上有些地方拆迁,有你们厂子的地方吗? 谁知道呢,现在正改革开放,天天在变,农村都实行生产责任制了。 李哲端着饭碗,要吃。翠花突然想起来说:小李,你喝酒吧。李哲受宠若惊:啊,我不会喝酒。随后,就扒了一碗稀饭,也不言语,撂在那。翠花歪着头问,吃饱了吗?又去拿他的碗,要给他盛。李哲一拦她,吃饱了,谢谢姐姐的盛情。翠花的孩子哭了,她忙去哄睡了孩子。 吃过午饭,姐姐姐夫要去上班,孩子上学,学校就在附近。表姐怀疑妹妹有点猫腻,也没多说,姐夫就说,我先走了。翠花忙把他们叫住:姐夫,等一下,我要和你们借一千块钱,等我回家拿了再还你们?无需避讳,她也不怕李哲听着,今天偶然的碰到一起,再见面,不知何年,决心把他那一千元钱给他,才带他来表姐家。 做啥用啊?表姐问。 给他!翠花指指李哲,我借了他的钱,很多年碰不上他,今天碰上了,想还他! 表姐说,行,家里可没那么多,我下午去支。 李哲直摇头,我不要,那钱,是我给她的。 翠花说,姐,你支吧,我一定还他!我们等你!李哲说我不要了,我这就走!翠花急了,你不能走,等姐姐回来! 表姐、姐夫、孩子都走了,翠花的孩子在睡觉。风,抽的门,来回的咣当!她看李哲要迈出门槛,一个箭步,一使劲,就给拉得扑了她个满怀!翠花立足未稳,倒下去,他实实地压在她的身上,两片鲜红正准准地叠印在一起!
七
两个人同时感到很尴尬,李哲红了脸,赶忙用手撑地站起来。翠花的脸腾地红成了一块大红布!像一团火,燎得李哲倒退了数步。翠花定了定神,拍打身上的土,说:你不能走,等姐姐回来。她跑到他的后面,用后背倚住了门,手迅速地伸到后面,摸到门插,嘎巴插上了门。他转过身,看她呆呆地倚在那,说:我不走了,我回里面坐着,你也回来吧。真的?嗯。 外面,一阵紧似一阵呜呜的风声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在那里鼓着。翠花耐不住,拿姐夫的半导体,听里面的京剧。 春分时节,天还是比较短的,学生早早地回来。孩子对翠花姨说:我给你们念课文。就一字一句地朗诵起新学的《温暖》: 天快亮了,敬爱的周总理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他为国家为人民又工作了整整一夜。 周总理刚要上车,看见远处有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街道,他走过去,紧紧握住工人的手,亲切地说:同志,你辛苦了,人民感谢你。清洁工人望着敬爱的周总理,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一阵秋风吹过,从树上落下几片黄叶。深秋的清晨是寒冷的,周总理却送来了春天的温暖。 李哲独坐在一边,着急的没法,他恨不能一下子就到父母身边。 下班的回来,一齐被风卷进屋,都用手拍打身上、头上的土,都说,太脏了,啥天呀! 翠花孩子醒了,她抱着,问:姐,钱支回来了吗? 嗯,支回来了。就数给翠花。 李哲还是推辞不要,翠花硬塞在李哲的棉衣兜里。 都很累了,表姐做口饭,大家吃完,就安排睡觉。当然,李哲和姐夫在外面,姐姐、翠花和孩子去里面的套间。自打翠花来了,就让翠花和孩子住套间,姐姐姐夫住外间,在外面当门卫。今天李哲来了,姐姐当然去妹妹那睡,李哲和姐夫一个双人床,睡电褥子。屋里的格局是这样的:进了门,是锅台、灶,边上放一个厨子,左面里屋是个火炕,对着有个哑巴口,用门帘子挡着,李哲和姐夫就睡这里。姐夫有个习惯,爱听八点钟刘兰芳讲的评说《杨家将》,就在床里面,待李哲脱衣躺下后,拉灭了灯,摸着糊在那里鼓捣收音机,听完了,闭了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李哲的棉袄在腿下扔着,薄薄的棉裤也在下方扔着,人却不见了。 风,无休止的刮,黎明要到了。 蒙蒙亮时,姐夫一看身边的李哲没了,赶紧爬起来找,差点把床头的收音机碰到地下。小李小李 翠花和姐姐听到喊声,赶紧穿衣服,也跑出来。 姐夫说,夜里,窗户让风刮开了,我关了一次窗,我迷迷瞪瞪的,忘了他在不在了?用不用报案啊? 翠花说,尽瞎扯,报啥案?你快去厕所找找。 姐夫答应一声,往外跑,门是插着的,他一定是跳窗走的。风,嗖嗖地吹了进来,好冷。厕所没有,马上就折回来。翠花和表姐非常焦急,看看李哲的棉衣都在,掏掏他的钱也在。他不会就这么走的!姐,你们还得上班,你做饭,我和姐夫,分头去找!两个人又一次扑入狂风中。 风,刮了一宿,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刚刚返青的白杨的枝干,来回地摇曳,折落残枝。垃圾堆里的灰土、烂纸疯疯癫癫地打着旋,肆无忌惮地舞蹈,像大海里的巨浪拍打着礁岩,一阵阵无休止的洗劫、涤荡! 翠花没顾得扎头,头发吹得零零散散,慌慌张张地像雷雨前黑压压浓浓的云团,因为风是乱刮,一会跑到脑后,一会遮盖了双眼,让人很是着急,两只手紧地往后抡。她像个疯子,大步流星地边跑边喊:小李李哲任她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女人娇嫩的声音,根本抵不过风的咆哮,喊多少声都被风声吞噬淹没了。 跑了有五里地,终于在一条污水沟旁的一棵老白杨树下,发现了李哲。他身着米黄色衬衣,蓝色衬裤,脸上毫无血色。翠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摇晃着喊:李哲!李哲不论咋摇,他都死一般沉寂。 她站起来,哭哭啼啼地喊路人,跪地下求路人,救命快!救命!
八
正是早晨上班和上学的时候,过来两个工人,帮翠花背起李哲回了家。跟前没有车,离医院又远。把李哲放到床上,给他捂上大被,翠花去找医生。表姐对翠花说,摸他的胸口是温的,肯定是冻的,我们上班了,你找医生看看,不行,就去食品公司找我们。翠花不知所措,答应着。孩子还睡觉,她跑出去找医生。医生摸摸脉,说,他是冻的,大被盖严实点,捂着吧。医生走后,翠花呆呆地立在床头,傻傻地瞅着李哲。有半个多点,李哲也没缓过来,摸摸他的手,冰凉! 妈呀!翠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不会死了吧? 真是万般无奈了!她又故伎重演。她搬了几次他,他都头朝里直挺挺地搬不动,今天是咋的了,咋没有劲了?不是那个年头了!翠花捋捋乱七八糟的头发,自己已不年轻。她急死了,去头那边抬,那边有墙挡着,把翠花弄得一身汗,她真是急死了,咋办? 不!我一定要救活他! 她急忙的脱掉外衣,也不管被汗水粘在身上的衬褂了。解开扣,下面只穿三角裤。上床后,俯下身,把李哲的上衣扣子解开,把大被拉到自己的身上。趴在李哲健壮的胸肌上,死死地抱住他,凉得翠花颤栗了几下,同时,两个如胶似漆的身体粘连在一起!翠花从来没敢正视过李哲,她刚刚发现,他很英俊,尤其是嘴角那颗大大的美人痣。 如果说,李哲这个时
北京治疗白癜风去哪里候,父亲千方百计地寻他不着,得知儿子失踪失声痛哭、欲死欲活无法控制心脏病的时候,翠花就是李哲的再生父母!也奇怪,翠花的孩子醒了,没有哭,只是躺着自己玩。一上午,翠花就一直用身体去医治他、融化他,她的热能在他的身上传遍。开始翠花扳他侧身,怎么也无法抱紧他,只得趴在他的身上。李哲渐渐苏醒时,彼此身体散发着热量,翠花才侧身用一只臂膀搂着他,另一只手只好压在身下。 那是一九八零年春,接近午时,李哲诞生了他的第三次生命。他嘴里不停地叨叨:爸,爸爸。这时,翠花赶紧爬起来,穿衣服,长出了一口气。大被仍然蒙在李哲的身上。 李哲终于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被油烟熏得斑斑驳驳的黑白相间的顶棚。翠花动一下他,喊一声:喂!李哲!你怎么了?他好像才反应过来,摇摇头,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猛地起来,见衬衣敞着怀,啊了一声,忙扯过被子。我就睡到这时吗?脸上扬起太阳的红润,太阳光早已勤劳地顺着门边的窗子照射进来,尽管风没有止。它像一个温暖的大火球,透过白杨的枝干,照射在床上、被子上,洒在地上一片片扑朔迷离的光。 你知道咋了吗?你又和上回一样了? 你说什么?他开始找衣服,翠花给他递过来。李哲不好意思地说:你先出去一下,好吗?翠花笑了,心的话,刚刚都啥样了?还害羞?她上了里屋,抱起孩子。 等他穿完了,翠花过来问:你想起什么来没有? 刚才你说我和上次一样,我一点不知。 你夜里跑到外面去了,知道吗? 他仍摇头,浑然不知。 你想想,是不是你以前有过这种毛病呀? 他竭力地想了半天,我觉得爸爸在到处寻我,到处喊我。李哲急得从床上下来,我要回家,去找我的爸妈!也许是血缘关系吧,这时正是李哲的父亲找不到失踪的李哲,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想起来了,那年八岁,夜里下着雨,爸爸的一件漏雨衣,裹着淋透了的朦胧的我。爸爸说:找到我时,我正抱在一棵大树上,恍恍惚惚,什么也不知道。今晚,我就是觉得雷电交加的,爸爸在喊我的名字! 翠花嗔怪地说,是我喊你的名字! 李哲真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他掏出那一千块钱,塞到翠花的怀里,诚恳地说:不管咋说,你的恩德是这些钱没法报答的,你还是留下吧。 不!翠花说,你拿着它治治病,再这样很危险,你认为杀了人,觉得命不算命,你还有亲人呢,你不考虑他们吗?他推辞着,我没病,看啥? 翠花分析说,你想想,你杀人那天夜里是不是也这样?李哲想了半天,我觉得是真的。 那好,你认为是真的,就得面对,你回凌钢找你最好的朋友,偷偷地问,那个人死之后埋在哪里,有没有人告发你,查证一下。李哲若有所思,你说的对,我先去找爸妈,然后去查证。
九
翠花回到村子,就听到了流言蜚语。 栓子找了个女人过了好几年,是千真万确。翠花不依不饶,栓子怎么解释,她也不听。大女儿都出嫁了,在外地打工搞的外地人,很远。儿子上了大学,如今,就是他们俩了。可是,因为感情不和,翠花误会栓子,两人天天吵。时间不长,翠花在村办厂子上班能干,被村里选上了村民组长。那天气不过,栓子把翠花打了,翠花一气之下,跑到干姐姐那里住了下来。 翠花的村民组长事情也很多,给组里各家各户抽自来水啊、办保险啊、合作医疗啊,反正忙得不可开交。 翠花自己花钱买个电动车,手机,用着方便。 一天,回来晚了。到营子头,正碰上栓子赶车回来,他看见翠花,便扭过头不搭理她,兀自抽打着牲口,嘴上不说好听的,故意对着牲口谩骂牲口被他狠命地一打,奋起四蹄,稀溜溜叫着超过了翠花。 翠花正在气头上,听着栓子在骂,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仇恨,扔下电动车,一下子窜上车,两只手一齐揪住栓子的耳朵,嘴里骂着栓子的妈,喝问道:你骂谁? 扑得过了力,一下子把栓子推到地上,自己也跟着压到栓子身上! 栓子防不胜防,不知道翠花的,身子被重重地掀下来,手里的鞭子也压在怀下。耳朵和耳朵边上的肉火辣辣地疼,身子实实在在地砸在地上,把大地砸个大坑,尘土呼一下飞起来!他嘴吐着土,手撑地想翻起来,翠花得了地利,正好骑在他身上。他佝偻着,想翻也翻不动,翠花本来就憋着气,谁知栓子指桑骂槐,这一下,把气愤都发泄在他身上,照着他的后脑勺一顿扇,嘴里嘟囔,叫你骂!叫你骂! 栓子哎呦、哎呦地叫,我也没骂你,骂牲口呢。 翠花打累了,一边起来一边说,你还犟嘴,又踢了他一脚,回身跨上车子就跑。 栓子慢慢地爬起来,灰头土脸,嘴里吃了一口土!眼睁睁看着翠花跑远,这个气呀!
十
严酷的冬天,老哈河的水面上结了冰,栓子戴着早年的狗皮帽子,帽子带系得紧紧的。披着旧的带着栽
白癜风治疗医院绒的蓝色棉大衣,戴着棉手套的手握着用破三角带拴的短鞭,抽打着那匹白色的马。这些日子天冷,栓子在城里拉脚,天天给人家倒煤(霉)。他把缰绳拴在车耳朵上,跟着车跑,免去冻脚。 翠花骑着电动车,去镇上办事。慢慢地前行,路上积雪被太阳一照,夜里一冻结成锃亮的冰。她的腿长,小心翼翼的,不好走就用腿支着。 栓子离车很远,在马车后面悠闲地过老哈河。 他想都没想到,还是从原来那块冻死的冰冰上赶的车,怎么走到半道,车就咔嚓一下掉进冰窟窿里呢? 马扑腾了几下,由于拴在辕子内,动不了了。 腰别子(手机)泡在水里,大衣也落入水中。人不该死终有救。终于有人骑车过来了,栓子远远地瞥见了,赶忙转过头,就是死,我也不用她呀!谁呀?翠花。他陷在河里很久了,四面都是漩涡,冻得浑身哆嗦,余光中,他看到翠花在放电动车。呸!看她干嘛?她能管我?栓子想错了,谁知翠花不顾一切地朝这边跑,一边跑,一边喊:栓子栓子 栓子的脸突然变了,他的泪要急出来,扬起一只手直摆:别过来,不要过来 栓子怕翠花也陷在泥沼里。 翠花听到喊声怔住了。但已经涉入水中。 栓子此时忽然想起村人讲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曾经有个妇人在河边洗衣,水中便旋起了漩涡,就把女人卷走了是王八精干的!一想到这,吓坏了!不能让她下水啊,卷走我一个人不能拐走翠花啊!他非常清醒,连八月节打翠花,到领回吴丽丽都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他的身体开始往下旋,脚下越动旋下去的越深 翠花撕破嗓子喊:你为啥不让我上去,我拉你上来啊,你还记着以前的仇啊! 栓子吼着,不是,别过来,过来就是送死,你快打手机! 翠花想起干姐姐家的金杯车,就打回了电话。 不一会,金杯车果然来了。翠花不敢再往前去,栓子沉得只剩个头了,下颏靠着水,眼看支持不住了。 司机和几个人就开始扔大绳。扔到翠花跟前,翠花又狠命地往前抛。一下下的激起了水花,终于把绳子扔到了栓子的上头,头部把绳子截住了。栓子咬住牙,把绳子拴在腰上,大家像拔河一样给他拽了出来。
十一
吴丽丽返城后分配到一所中学,认认真真地工作了很多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一直没有答应,最难忘过去那段时光。放寒假了,她想只身去看看栓子,一大早,就踏上了班车。 栓子的家她再熟悉不过,在这里住了四年。栓子的屋门上了锁,她从砖空里找到钥匙,进了屋。看来,栓子的媳妇翠花还没有回来。吴丽丽叹息一声,咳,栓子啊。 栓子的屋里很乱,吴丽丽开始打扫。正在这时,外面狗咬,她探头看看墙外,来了一辆车,车上很多人。她赶忙躲到那边没人住的屋里。 车上下来两个人,抬着湿漉漉的栓子进了屋。就听人说:栓子,行吗?栓子答:行。把栓子放到大炕上,蒙上大被,就坐金杯车走了。 吴丽丽跑过来时,栓子昏迷了。她扯开大被一看,这哪是人啊?分明是一条鱼啊!她顾不得羞臊,给栓子脱衣服,来回翻栓子,弄了一身汗。栓子仍然不醒,她就跑到外面抱柴草烧炕,让热气充塞房间。再看再喊栓子,栓子就是不醒。他会死吗?她想到这,吓了一跳!忙跳上炕,解开自己的衣扣,敞开怀,两片胸肌贴在一起。她把他搂得紧紧的,想用她的温度熔化栓子的身躯,把所有的温暖给他。 翠花的裤子也弄湿了,去干姐姐家换。她和栓子怄气,不愿意回家。她以为栓子挺大的人,回去换了衣服就没事了。当她换完衣服时,就有点着急了。干姐姐说:翠花,看你魂不守舍的,着急就回去看看吧。 嗯。翠花答应着,我这就回去。她回到家,看到了这一幕。她破口大骂这个女人,不要脸,养汉精! 栓子醒过来了。吴丽丽也被撕扯到地上,整理着衣襟,脸色羞红。 翠花翠花 翠花在屋里骂吴丽丽,李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喊翠花。 李哲澄清了过去做过的一切。今天出差,路过这里,想过来看看翠花。 吴丽丽一看是李哲,悲喜交加,骂道:李哲,你还活着? 李哲处过的对象就是吴丽丽,两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十三年啊,他曾为她打抱不平,梦游杀了人后就杳无音信。 翠花看见李哲,那种情自然抵不过吴丽丽,刚要去拉李哲,吴丽丽跑了过来,抱住李哲哇的一声哭了。
(散文编辑:江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