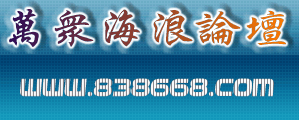高一时无聊时写的
照相.葬礼
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入感受、亲近生活的方法,于是,曾在文字里苦苦寻觅,终于经不起大涛大浪的排煞。
不知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初遇这张让全世界震惊的照片 某天,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倾心的对象。尽管她只是一个受人蔑视的老女人,一个苦苦守着她的肮脏却有条理的摊位的菜贩子,可她给我的印象永远也抹不掉,我似乎和她相识过。在冥冥中的某个刹那,我就记住了她的样子。我欣慰地抬起相机,等待着一个老人在生活中最零丁的一个POS。可是,许久不得,怪天气太过晴朗。
第二天一清早,我悄悄地赶来,注视了她好久好久。她很凶,当她一发现我,便呵斥问我盯她做什么。我自然有点害怕,那是不由自主的畏惧。她也许有点我祖母的影子 “我为什么要让你拍照?你是我的儿子还是孙子?”她很窘迫,但很冲动。我也意识到她似乎被什么给刺伤了。
我想起了撒娇一招,可刚当我走上前,没想到,一盆冷水泼上了我的身子。我连忙用袖子拭着相机上的水,无奈地走开了。当时,我很气愤,也真想哭。可能这将成为我平生受过的最大的耻辱之一。
第三天,我加入了一个大学的摄影社Opera S”。社长看我才中学生,对我的要求并不高,入社的交的第一份作业可
三元生物治疗白癜风咋样以是一张简单的风景照。我向社长承诺,自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但当我一走出社团的门,一切都变了 我在第三次去那里的时候好好地伪装了一下 “我……我……我来买东西!”我把咬破了的烟扔到一边,把手指着莫名的野菜问道,“这个多少钱?”
她的表情带着怀疑与诧异:“哦。2元钱1斤。”
“这个呢?”
“1块5。”
“那个?”
“3块。最贵的!”她有点不耐烦,“你到底买不买?不买的的话,给我走开,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我顺音“唰 她可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算了钱。
“那您能不能让我拍张照啊?”我恳求道。
她闻声便有伸手去那水盆的趋势,我一见情况不妙,撒腿就跑。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就算我长得不够迷人,但我这样奔波了n天,难道她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难道我就连这么一点拍张照片的小事都办不成?”
时间大概又过了两三天,摄影社里要交作业了,我当然没有可以交的。后来社长催要也没交上,我就被开除了社员籍。社长把我开除的当天,我还和他吵了一架,吵完架后愤怒地跑上了大街上。雨下得很大,当雨水还打湿我的相机时,我觉得无比委屈,可我任它在我的相机上怎样地流淌。复杂的心情让我忘记了自己是否在那场雨里哭了。尔后,我不由自主地径直奔往那条让我伤心的旧巷口。
天色黯淡得很,才发现,那位孤独的老人还蜷坐在自己的摊位旁。整齐地放着的还没有卖完的菜、挂着旧油灯的大伞、她背后发廊的玻璃墙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店主……天气一点也不冷、不冷,可我怎么就看见她张开的嘴冒出白气?不知那是冷的,还是热的。
我举起淋湿的相机,把焦点聚在她的脸上,等待着那个让我奔波了n年的瞬间的到来。终于,我第一次找到了,我使劲地按着快门,一连拍了七八张。
她觉察到了我的存在。“过来!”她拉大了嗓门喊。
我本想拔腿就跑,但我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可能是我为自己已经得到我想要的而窃喜,可能是我累了,可能是我听出了那阵呼喊并没有平常那么刺耳、恐怖。我慢慢地走上去。
“这是怎么的?”她指着我的脸上说。
我顺手摸过去,在眼角有一阵疼痛感。我才明白,眼角上已经肿起来一块。我也不免有点担心,因为那应该是在珠宝店的玻璃墙上撞的,真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把珠宝店的墙给撞出了一条裂缝,珠宝店的人是否会把我当成强盗。
“移近点!”她抓住我的手,“怎么不带伞就跑出来了?”
“我……忘了。”我本来想说自己出来的时候还没下雨,但是知道自己的手已经冰冷的时候,也就这样回答了。
“那你饭吃过了没有?你的手好冷啊。”她把手握的更紧了。
“没有……不,吃过了!”我有点晕。
“那饿了吧,我带你去吃面。”
我跟着她走进了旧巷子里的一家小吃店。说是吃面,她却包罗了一桌的好菜。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根本没带钱
如何使肌肤不在感到口渴。便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带钱!您帮我付了吧。”
“我请你吃,当然我付钱。”她回答说。
“哦。”我越来越不安。
……
我们一起吃饭的那天,她喝了许多酒。第二天,我带了洗好的照片去某地参加了某届“某某杯”艺术照比赛,获得了最高奖。
第三天,我回来了,我匆匆地赶去巷口……
我下了公交车,巷口并不见她的人影,摆摊的是另一个女人。我上前去问情况,她不知道,她说她看这里没有人摆摊才来的。我又看看路牌,的确没有走错,于是跑进了巷子,闯进她的没上锁的屋子里,疯狂地喊了一阵,没有回音……
我沮丧地走出门,心里不知有多郁闷,隔壁的一个老头告诉我说,她昨天一大早就被医院里的救护车载走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就跑出巷子,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开进最近的一家医院,可没有给钱,我管不了司机在车里怎样乱喊。
一当我冲进医院的大厅,便传来了熟悉的叫骂声,我不知有多欣喜,她果然在这里。
“你们这群强盗,我没有病,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你么这群土匪!……”听清这段话,我有点伤了,我感受到了她的压力。
她看见我在大厅里站着,就跑了过来,医生、护士也来了。“你来干什么?”她问我。
“我来找你。”我说。
她止住医生和护士,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医院。我也跟了出去。
我追上去说:“这是给你的,我拿你的照片参加比赛,拿了2万元的奖金。”
她瞥了我一眼,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孙子?”她把我递过去的装了1万元的信封扔在了医院里的广场上。我的眼泪瞬时划落。
“我明天要去日本看我儿子。”她假装释然地说。
“嗯?……”我愈加心痛,眼泪不停地夺眶
患有白癜风植皮治疗行不行而出,“那我送你去机场?”
“啪!”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我是你的谁啊,你为什么送我?现在的孩子真没了管教!”她转身走开了,不停地嘀咕着什么。
我傻傻地望着她那憔悴的背影,一只脆弱的臂膀抬起又放下,我知道她也在抹泪,她在想自己过世的儿子,在向我倾泄她所有的怀念带给她的痛苦、寂寞带给她的苦闷,还有对我像对待亲人一样的爱,甚至是母爱或是对孙子一样的爱。
之后的一天,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了n部喜剧,可我没有笑。我只是两眼直直地盯着屏幕,看见一个孤独寂寞的老人在贫窘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一盆水倒在我身上,一见到我便破口大骂地把我赶走,却又花掉所有的积蓄,几十年来,第一次和别人吃一餐饭……
而我,正在躲避一个安静的灵魂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