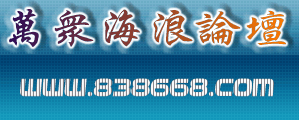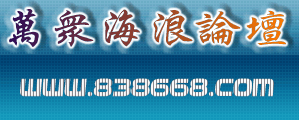谁可相依
天很阴晦,有露珠在浅草里捉藏打发寂寞。
父亲坐在自家门前的石条子上,头顶着一大片乌黑的下坠得很快的云彩,专心的在吸着他的旱烟。
我知道,父亲在生我的气。
昨天晚上,晚饭开得很早。父亲和女儿随后在看着动画电视,妻在收拾着桌子,我呢,难得清闲的看着一份杂志。
那晚原本没有什么特别,也许再过一两个小时,各家各户的灯就会次第熄灭。窗外香樟树很安静的肃立,没有风,看不出要下雨的意思。
即便没有征兆,该来的依然要来。
父亲很踌躇中说出的一番话,是伴随着窗外很细密的雨点声传进我们耳鼓的。
“爸,您都这大把年纪了,还……给我们留点面子吧。看看村里的,哪个大伯大婶有您这想法?”妻是直肠子,说话不会转弯抹角,“真要是这么做,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不孝敬您,把您往外赶呢。这罪我们可受不起!”
我白了一眼妻。她正说到兴头上,没注意。“要是我们做得不对,您开口说还不成吗?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那闲心,不给自个儿添累吗?任谁答应了,我也反对,咋说我也还想顾着这张脸呢!”妻越说越来劲,碗筷杯碟相碰的声音比往常更清脆了些。
被儿媳抢白一通,父亲不惊诧,这早在意料之中。他只是很专注的把目光投向架着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我身上,他相信受过高等教育自己最宠爱的儿子一定会赞成自己的想法。前些时他也很委婉的向我表达了需要我支持他的意思。我当时的回答虽然很含糊,好像模棱两可的意思多了一些,但父亲从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倒的一大通苦水应该是有效果的。
父亲的逼视,让我踌躇。我感觉出了自己的举足轻重而又无可闪避。我突然发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风口浪尖的一艘小船,根本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沉或浮都在转瞬之间。
从内心来说,我很赞同父亲的想法。父亲老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密布,那双梳理岁月的大手黝黑而偏瘦。我更明白,这些表面的苍老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心灵的孤寂才是最要命的。父亲原本就不爱说话,母
专家警告花露水的使用不能随便亲去世,他的话就更少了。按理说,找个老伴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妻的反对也是有道理的。接近六十岁的父亲原本就该在儿女身边安享清福。儿大女成,孙儿绕膝,儿女们知道父亲受过的苦累,走过的艰辛,谁都抱了一颗回报之心,不会让父亲受丁点的委屈的。父亲可以很惬意的打发岁月,看朝阳升起,
专家能否告诉我北京有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算是最好的呢瞧林间晚霞,串串门,嗑嗑家常,多不好?可是父亲却横生枝节,说要找个什么老伴,原本很融洽的一家人忽然得冒出个人来,儿女们的心生生的悬了。
更重要的是,父亲找的老伴是别人倒好,却又偏偏是婶,还说什么要到婶那边去住。
除了让父亲失望,我好像没有更好的选择。
雨更大了。
婶的名儿早被人们遗忘,甚至她家住哪里我都不很清楚的记起。在我很遥远的记忆中,她一直是我老家七弯十八拐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在她结婚的那天,四乡八岭的青壮后生都张着一双充血的要冒出火的眼,几多羡慕几多愁怅。直到今天,婶依然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新娘。
我不是很喜欢婶,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个大男人在她结婚的头一天,避了众人,和一个女人,躲在麦草垛里,很伤心的哭。而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
那时我还小,我不知道我的伟岸而又坚强的父亲怎么会脆弱得不如干瘪的麦秆,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偷偷的哭。
婶之所以在我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嫁给了瘸腿王叔。
叔瘸腿而多病,像一株病怏怏的黄瓜秧,随时都有被烈日烤焦的危险。也许是他坎坷经历比别人多些吧,命运奇迹般的把花样的婶赐予了他,使得他觉得自己所受的所有的不幸都在情理之中。
叔不感谢命运,他感谢和他从小光屁股玩大的父亲。叔自个儿没有孩子,所以更爱孩子,老大的人了,还和我们小孩一起玩。有时我们便会问他:“叔,婶咋会看上你呢?”他便总是憨憨的笑,说:“得谢你爹呢。”再问,便不说了。两只虎牙像犁铧的齿,搁在很厚的嘴皮上,很滑稽又很可爱。
父亲和婶有故事。
故事是一点一点从母亲的嘴里套出来的。
母亲是个谨小慎微的女人,她不大爱说话,我总觉得母亲终其一生好像都在担心着什么。后来我才明白我的这一直觉是非常正确的。
在我小时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是方圆几道弯里最有学问的人。他是当时家乡唯一到县城最高学府上过高中的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龙飞凤舞,闲空的时候父亲还会时不时地写一些打油诗自娱,而且身材单薄斯文十足的父亲还是一个庄稼好手,田里农活他是样样精通。
听母亲说,父亲的悟性很高,上高中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教他的老师几乎不止一次很肯定地对我的爷爷说:“准备好上大学的钱吧。”爷爷听了很高兴,那几年的冬天,倔脾气的爷爷坚持没杀年猪,硬是把猪卖了,凑着一个一个的钱角子。只是父亲没让爷爷满意,因为他好上了现在的婶。
年轻时的婶和父亲同班,而且有一段时间同桌。父亲的伟岸和文雅征服了美丽的婶。那时的社会还不太开放,校园里的恋情还是凤毛麟角,可是我的父亲和婶便能够顶着众多分不清是艳羡还是鄙夷的眼光,以及老师耐心的规劝和不乏直面的批评,堂堂正正的走在学校高大梧桐下的林荫道上,有时也能在远没有现在这般光怪陆离的县城街道上手挽手的溜达,引起路人侧目。
也许爱情往往会让人沉靡而丧失斗志,当爷爷的钱角子逐渐鼓胀着他的希望时,传来的却是老师一次次无奈的叹息。父亲的成绩一落千丈,勉强混了个毕业证便惭惭的打道回府了。
一同回家的还有婶,父亲原本以为自个儿学业差劲,可是能领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回来,爷爷一定会高兴点的,至少不会发火。然而父亲错了。手牵手很亲密的他们被吃着浓浓自家旱烟的爷爷堵在了门外。被烟呛得咳了几声的爷爷只对婶说了三个字:“你回吧。”然后是用旱烟斗狠狠的敲了几下父亲的头说:“给我死进屋去。”父亲不敢违逆爷爷,乖乖的回到自己的屋里,身后老式的木门“吱吱嘎嘎”的作响,然后“咣当”一声关上了。
父亲的爱情就这样草草收了场。
父亲当然不会甘心,可是不管他是哭是闹甚至是绝食都倔不过他的亲爹,爷爷说什么也不会允许一个破坏了他伟大梦想的人进入他的家庭。爷爷快刀斩乱麻,很快就用准备让父亲读大学的钱把我的母亲迎娶进了门。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因为她知道,父亲的心里也许永远都会装着另一个女人。
而当那个女人时隔六年后也嫁到了我们村,母亲的危机感更浓了。甚至我父亲也看出了母亲的担心,他有几次很怜爱的打趣我母亲:“我要是想走你还留得住我?那闲心干嘛?”
我明白母亲的忐忑,特别是瘸腿的叔结婚头一天,我亲眼看到我的父亲和一个女人躲在麦草垛子里哭,母亲的忐忑就深入了我的骨髓。
那个女人的背影像极了婶。
天
北京最好的中医治疗白癜风医院是哪一家呢仙般的婶怎么会嫁给瘸腿多病的叔,这也许是个永远的谜,或许它也不算是什么谜。不过我父亲结婚后婶仍然痴痴的等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父亲结婚后的头几年所穿的毛衣都是婶寄来的。我的母亲织的毛衣比她的好,而且为父亲织的很多,可是父亲不穿,于是她只有把它改小给我们穿。但是母亲每次总是按照父亲的身材做,父亲不穿再改,从不先织成小的。虽然明知父亲是不穿的。
婶嫁给叔,使得萎靡多病的叔振作了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叔很是高兴,他总爱叫我们小孩子到他家玩去。婶总会拿出糖啊什么的给我们吃。有时候,婶会定定的看着我,好几次我都不好意思地躲开,身后便会传来婶的喃喃低语:“真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可惜好景不长,叔的病很快就重了。叔吃打针婶都是很负责的监督,半点不由叔马虎。就是在叔病重时,婶也是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守着。叔临死时我和父亲都在他身边。他很平静 ,说因为婶,他这辈子没白来。只是没有给婶留下一娃半崽的,让婶孤单,他很难过。弥留时,叔一手握着婶的手,一手握着父亲的手,看着父亲很吃力说:“拜托了,帮我照顾好她哈。她一刻都没忘记你呢。”
婶从此独身,像一只候鸟。
几颗玉米粒大的雨点敲打在地坝上,石条子上的父亲动也不动。他的眼光,掠过门前几块弯弯的梯田,爬上对面的小山冈。在小山冈上的那片不大的林子里,几棵桂花树下,有我母亲的坟。
雨点渐渐密了,像一片雾,漫了过来。我叫了一声父亲,没有回应。我把伞撑在父亲的头上,父亲还是没有发觉。也许是他发觉了,只是懒得理我吧,总之没有回头。
我俯视着父亲,看他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摇。我想起小时侯父亲总把我扛在肩上。有一次,我发现父亲的头上有一根白发,我就对父亲说:“爸爸,你长白发了也。”父亲叫我给他扯掉,可我总是扯不掉,因为我怕扯痛父亲。看着眼前失落的父亲,我明白,就算我扯去父亲满头的白发,其带来的伤痛,也远远不及昨晚我婉拒父亲给他的伤害的万一呀。
“爸,回吧。”我说。风刮起如丝的雨点,横冲直撞。“遮不住了,进屋吧。”
父亲抬起头,用一种很陌生的眼神看了看我,然后伸出黝黑而瘦的手握住伞柄。你回吧,我出去走走。
看着那伞在风雨里像一个趔趄的老人柔弱的飘摇,然后渐渐变小,成为一点,最后孤独的消失,我蓦然发觉:一夜的功夫,我的父亲老得好快。
难道我错了?
妻在屋里张罗着饭菜,有很浓的糊辣椒味从厨房荡进堂屋。我看着父亲刚才坐的那块条石,被雨水涤荡得发亮。
雨在风里乱舞,把我的思絮扯乱。
我不由地想起了麦草垛儿,想起了那紧紧相拥的两个人,想起了为不伤害母亲,我是多么辛苦的保守着这个秘密……
我也想起了我的母亲,一生都在担心丈夫被人夺走的小女人,是怎样提心吊胆的过了一辈子。我想她即便是死后也是不希望悲剧发生的吧。
我当然也想起了叔,想起了叔临死时说的话,想起了叔离去时的平静和坦荡。也许死者长已,生者才更需要宽容和理解。
也许母亲也不愿看到我的父亲孤独的活吧,我不由想。
我起一把伞,抢步冲进雨里。
母亲的坟在风雨里静默。
父亲不在。青绿的浅草里有丢弃的旱烟,我还能感觉得出它辛辣的味道在湿漉的空气里弥漫,我甚至感觉得到我地下的母亲因为这味道而睡得更加安稳了。
父亲的脚印很清晰的显示了他的来和回,山里岔路多,错过是很容易的。
忽然,在那丢弃的旱烟旁边,在很深的泥泞里,我依稀看到了几个字。那一刹那,我的心像惊涛拍岸,有咸咸的海浪汹涌的漫上眼眶。
那几个字是:谁可相依?